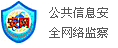[61]传统上中央与地方之间主要是自上而下的关系,采取命令—服从或委托—代理模式,但从治理的内涵出发,央地治理可以是自上而下的,但更多的是平行的。
修订《领导干部自然资源资产离任审计规定(试行)》、《党政领导干部生态环境损害责任追究办法(试行)》,强化生态环境保护硬约束。完善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推动新时代多党合作更加规范有序、生动活泼。

完善跨境腐败治理工作协调机制,强化对海外投资经营等领域廉洁风险防控,一体构建追逃防逃追赃机制。坚定维护党中央权威和集中统一领导,制定推动《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工作条例》贯彻落实的配套制度,确保涉及全党全国性的重大方针政策问题,只有党中央有权作出决定和解释。(九)完善把党的领导贯彻到党和国家机构履行职责全过程的制度。(二十三)健全一体推进不敢腐、不能腐、不想腐制度。积极完善互联网+党建制度机制,注重运用信息技术手段推进和改进党建工作,增强党建工作的时代性实效性。
完善涉罪党员刑事处罚与党纪政务处分衔接工作制度,促进执纪执法贯通衔接。健全地方党委对同级人大常委会、政府、政协、法院、检察院党组实施领导的体制机制,加强地方党委对本地区经济社会发展和党的建设的领导。参见张绍谦:《刑法因果关系研究》,中国检察出版社2004年版,第35页。
[78] 参见2000年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执行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若干问题的解释》第12条。从考虑事项说的角度还可说明法院将起诉资格完全委诸实定法判断的特性。[89] 如此,笔者与周雷博士提出的法定职责——不利影响构成要件说的差异,仅在于法定职责要件的判断。[88] 应当认识到,如果起诉人仅仅请求行政机关答复投诉举报,此时不涉及第三人权利义务的变动,投诉举报人只需满足行政相对人的原告资格构成要件。
[41]就该两阶段构造,通常认为可以对应于我国的起诉阶段和实体审查阶段。黄宇骁:《行政法上的客观法与主观法》,载《环球法律评论》2022年第1期。

笔者认为根据《行政诉讼法》第2条第1款的规定,可将其中的因果关系要件分离出来进行单独判断。范志勇:《立案登记制下的行政诉讼原告资格》,载《法学杂志》2015年第8期。赵宏:《原告资格从不利影响到主观公权利的转向与影响——刘广明诉张家港市人民政府行政复议案评析》,载《交大法学》2019年第2期。[73] 参见李晨清:《行政诉讼原告资格的利害关系要件分析》,载《行政法学研究》2004年第1期。
笔者认为,从体系解释的角度来看有必要回溯至第2条第1款认为侵犯其合法权益的规定,探究第三人具备利害关系的意涵。因而,在笔者看来,就法的范围、权益性质的争议不过是规范要素型保护规范理论的内部问题。如果没有该行政行为,起诉人主张的损害一定不会产生,而即使该行政行为存在,通常也不会发生这种损害,可认为不存在因果关系。[57] 此是严格可能性说的观点,也是德国的通说。
从某种程度上来说,下述讨论的部分案例也存在运用保护规范理论判断处分性的解释空间,但是出于谨慎考虑不纳入研究范围。具体而言,运用保护规范理论判断合法权益和因果关系[5]等原告资格构成要件的模式称为主观要素型。

[33] 不过,在预防性诉讼和确认之诉中有将其判断标准理解为广义的保护规范理论的可能性。保护规范理论仅作为合法权益的判断标准。
我国学者的类似观点,参见何天文:《保护规范理论的引入抑或误用——刘广明诉张家港市人民政府行政复议案再检讨》,载《交大法学》2020年第4期。其中,最高院采用保护规范理论的案例共5件(包括刘广明案、关卯春案、李百勤案、联立公司案和徐玉芳案)。(1)判断对象为合法权益还是因果关系要件的争议是主观要素型的内部争议,这关涉到规范要素型与规范事实要素混合型,何者更为正当的问题。[99] 该公式意味着,第三人原告资格的判断标准为利害关系,合法权益和认为侵犯是利害关系的两个构成要件。[55] 参见[日]盐野宏:《行政救济法》,杨建顺译,北京大学出版社2008年版,第162页。就此而言,过去学界有关原告资格构成要件中因果关系被其合法权益吸收的论断仍有说服力。
[39] 参见王贵松:《论行政诉讼的权利保护必要性》,载《法制与社会发展》2018年第1期。[33]在这点上我国就与德国类似,并没有将权利保护必要性成文化,[34]故也缺乏运用保护规范理论论证权利保护必要性的实定法基础。
[43] 本文立足于我国行政诉讼法和行诉解释中有关起诉条件的规定理解我国的起诉资格。根据第2条第1款的表述,认为侵犯其实是利害关系的事实要素(因果关系要件),而合法权益则是其中的规范要素(权利要件)。
从学理上来说,若对因果关系采取了相当因果关系理论,其实证成的是实体请求权。例如在孔繁旸案中,法院直接的裁判依据为2018年《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的解释》(以下简称《2018年行诉解释》)第12条第5项。
比如,对饶思霞案若直接采用权利保护必要性的适时性标准[36],就可以直接得出申请人不具有诉权的结论,而没有必要添附保护规范理论的论证。[47] 参见赵宏:《主观公权利、行政诉权与保护规范理论——基于实体法的思考》,载《行政法学研究》2020年第2期。在德国法中,实体原告适格解决的是实体请求权的有无问题。其中,第二个问题的答案相对明确,即客观要素型将保护规范理论用于判断权利保护必要性其实是画蛇添足。
[83] 参见黄宇骁:《行政诉讼原告资格判断方法的法理展开》,载《法制与社会发展》2021年第6期。[15] 参见赖顺新等诉国家发改委行政复议案,北京市高级人民法院(2017)京行终3019号行政判决书。
[70] 黄宇骁:《行政法上的客观法与主观法》,载《环球法律评论》2022年第1期。[9] 该案对因果关系的论证为如果没有行政行为,起诉人主张的损害一定不会产生,但是有了行政行为,一般都会产生这种损害,即可认为存在因果关系。
[93] 比如,巴霍夫认为私权受损承认原告资格,是经由基本法上的一般行动自由为媒介发生的。[48]相较之下,我国《行政诉讼法》第6条仅将行政行为合法性作为审理内容。
然而,对2017年以后最高院和北京高院涉及第三人原告资格的案例进行梳理就会发现,审判实践对保护规范理论的判断对象究竟是合法权益、因果关系还是不成文的权利保护必要性存在较大分歧。[95] 笔者认为,法律关系理论,基本权利直接适用说、考量要求说等仍然是从法出发的解释论,因而属于广义的保护规范理论。[72]以此来看,当下的规范事实要素混合型并不适合于撤销诉讼中运用。[90] 王世杰:《保护规范理论的始源形态——布勒公权论的再认识》,载《行政法学研究》2021年第1期。
笔者所主张的规范要素型,不过是法秩序框架下法的发现的结果。故而,我们完全可以将法院的说理简化为,因为被诉行政处分已经失效,故不存在权利保护的必要。
在该条款预设的情形下,无论具有处理投诉职责的行政机关是否对被投诉举报人作为,投诉举报人均非处理行为的行政相对人。[58] 参见龙非:《德国行政诉讼中的诉讼权能研究》,中国人民大学2013年博士学位论文,第86-87页。
即合法权益不满足,因而没必要再进行因果关系的论证。部分学者认为原告资格=利害关系=保护规范理论,而不涉及因果关系的判断。